从“剖面”到“钻孔”
——《国家地质公园——解密天碑地书》创作谈
来源:国土资源报
作者:郭友钊
发布时间:2015-0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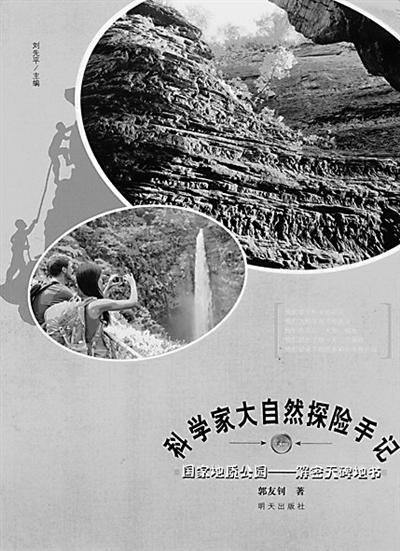
【作 者】郭友钊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5月
读书与行路,古而今,均是知识的来源。读的方式,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亘古未变。行的方式,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李白借助300年前谢灵运的木屐登上了山巅;“路喜到江尽,江上又通舟。舟车两无阻,何处不得游”,至今1200年前的孟郊欣喜舟车的方便,荒山野岭的柴门也有了车马客。这是旧行路的方式。李白想象,“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凭的是“轻舟”。但能够一日跑千里的“轻舟”,是现代的汽车、火车,一日跑万里是当代的高铁、飞机、火箭。这是新行路的方式。古人行万里路,需要大半辈子。富有想象的李白不得不“叹我万里游,飘摇三十春”。而今天去千里之外、万里之外,只需睡一觉的工夫。
“行万里路”,在增长见识的同时,可写成游记。徐宏祖坐轿、坐船,用了34年的时间游历华东、华北、中南、西南,大半个中国,写就《徐霞客游记》,登上了地理游记创作的顶峰。杨钟健骑骡、坐汽车、坐火车,在约10年的时间里考察了全国,著有《剖面的剖面》等三部游记,成了地质游记创作的开创者。但两人在行路中对交通工具的态度不同。未见徐宏祖抱怨轿、船影响游程,他一步一景,没觉得有什么遗漏的景物。杨钟健却多次抱怨坐汽车、坐火车没有自由,不能随心所欲下车去观察感兴趣的景物。两人的行路均希望一路连续观察,不希望其中存在间断。这种路线观察方式,杨钟健称之为“剖面”:“我这剖面,几乎是上自天时,下至地理,乃至人事沧桑,世态的炎凉等等,无一不乘兴会所至,都或深或浅地切剖一下。”因此,“这一本东西(指《剖面的剖面》)完全编好,照例也附有路线图……”
路线图是足迹留下的一根实线,那是有切身体会的行程。提倡新游记的杨钟健仍然能够为游记画出一张路线图,其游程的性质仍然与徐霞客相同,即使游程受到汽车、火车的困扰。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系统便捷使用之后,凭借它们行路的人们所有的自由只有在出“站”的时候。而“站”与“站”之间的“路”已成无感的“虚线”。可见,以“路线”或“剖面”为游程的游记写法,已不太适合于当代社会的旅行方式。
游程决定了游记的结构。游人一天或者一个周末可以游尽的地方,算为一站。一站,或许只是一个村庄、一座山头、一条山沟,面积数平方公里。写一站的游记不是应运而生。旧游记中除《徐霞客游记》、《五岳游草》等之外,绝大部分是写一站的游记。但旧游记的特点,正如杨钟健先生在《剖面的剖面》中所总结的,其中有不朽的好文章,如《桃花源记》,属文人的感时之作;但有的游记也记述自然,但所记不符合事实,甚至泥禁于古书,以讹传讹,这种情况俯拾皆是。为此,杨钟健先生提出了新游记:对观察的事实,进行真实的描述,佐以优美的文笔,成为适合于现代科学化的游记,能给读者正确的知识。
我认为,一站式的游记,既要写出该站的外貌,也要写出其质地,由表及里,尽可能写尽这一站的物事情理,不仅展示其美,亦要揭示其真,更要弘扬其善。要创作出这种游记,当对这一站进行“深剖”、进行“钻探”,形成游记作者窥探这一站历史的“钻孔”,以尽可能还原这一站的历史,包括自然的演化史、文明的进步史,以及记述这一站独有历史中的情理对现代人文的影响。
《解密天碑地书》是基于我对龙潭大峡谷游程的“钻探”,获得的一个窥视自然人文的“钻孔”而创作的游记,是自己行走以获知识的一种尝试。当然,也是我的一孔之见。
(作者单位:中国地科院物化探所)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43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4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