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深海采矿制高点
来源:国土资源报
作者:李 响
发布时间:2013-09-30
近年来,尽管我国在国际海底资源勘探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目前,国际海底活动的重心却在逐步由资源勘探向开采阶段过渡。我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与海洋强国的差距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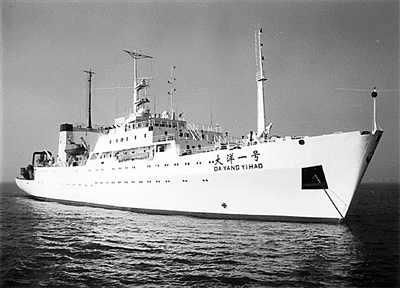

“蛟龙”探海,威风八面;同时拥有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这三种主要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专属勘探矿区,目前在国际深海采矿界还是唯一;深海勘查,持续见效,让国际同行为之赞叹……
几代海洋人对海洋强国梦的苦苦追索,让我国在深海资源勘探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是,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说,我们的脚步还是慢了一点。
9月16日,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尽管目前深海资源勘探活动仍十分活跃,但国际海底活动的重心已然向资源开采阶段过渡,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
“近年来,国际上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日趋活跃,并呈现出具有深远意义的新动向。一些跨国企业的深海采矿计划正在或已经付诸行动,深海采矿产业端倪显现,形势逼人。”在会议间隙,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金建才对记者说。
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与海洋强国的差距十分明显。“如果在这一步落后,就会步步陷于被动。而要迎头赶上,须从现在开始努力,须臾不能松懈。”一位业内专家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表示。
国际
准备充分且行动加速
一个事实已经不容否认:当我们还在资源勘探领域埋头苦干的时候,一些国家和国际矿业企业,已经对深海矿产资源的开采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
这依靠两股力量的推动:一股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陆地上的资源供给已经越来越乏力;另一股力量,则是海洋技术不断发展,深海采矿的技术和理念获得新突破。对深海采矿来说,技术的羁绊,显然已经越来越弱。
公开的报道显示,自2012年10月以来,一些涉及深海采矿的国际会议相继在中国举办,包括国际深海采矿第四十一届年会、第三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八十二条执行问题国际研讨会。
“这些会议,以深海采矿为主题或重要议题。关于海洋采矿可能比陆地采矿更环保、社会与投资效益更高等一些新理念和观点,正逐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对发展深海采矿,国际上不仅有殷切的期望,而且无论从技术支撑还是商业盈利的角度考虑,信心都越来越足。”金建才说。
业内的一系列动作,也在不断增强这个信号。
实际上,在2012年国际海底管理局第十八届会议上,制定深海采矿规章已被作为优先事项列入2013年的工作计划中,并期望于2016年前制定 (多金属结核)开发监管规则。其中重要动因之一,是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一批7个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将于2016年到期。
而欧盟前不久制定的《蓝色增长:海洋可持续增长的机遇》报告也明确提出,目前欧洲应主要集中研发各种深海和海底特种船舶及采矿装置,为联合开采国际海底的矿产资源作好准备。
不难看出,国际社会正加快做好深海采矿产业发展的准备工作,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战略部署上。“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国际矿业公司已行动起来,正积极推进深海采矿。”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
金建才告诉记者,在国际海底管理局成立并开始运作后的10余年内,只核准了8份矿区勘探申请。而从2011年至今,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有11份矿区勘探申请获得核准,另有4份矿区勘探申请待批,其中8份是西方矿业公司或其“借壳”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其商业目的十分明确。”
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和企业还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展了矿产资源勘探及开采准备工作。
记者了解到,2011年,加拿大鹦鹉螺矿业公司获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发的世界第一个深海多金属硫化物资源采矿租约,计划于2014年进行试开采。
2012年4月,该公司与我国铜陵有色集团签订海底矿石加工合作协议,每年向铜陵有色集团提供矿石110万吨,加工后的铜精矿全部销售给铜陵有色集团,合同期为3年,预计首次矿石交付时间在2014年。
此外,公开的资料显示,韩国的深海采矿财团也在汤加和斐济专属经济区内申请了矿区并进行资源勘探,计划于2015年进行一个年产30万吨规模的采矿海试。
“国际社会发展深海采矿产业,要具备两大要素——技术和市场。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两大要素已基本具备,而且推进形成这一新兴产业的行动在加速。特别是一些西方国际矿业公司,他们把中国作为未来深海采矿产品的首选市场,尤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金建才对记者说。
国内
需求巨大但能力不足
实际上,我国对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的需求同样巨大。
一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大宗矿产大量依赖进口,重要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铜约70%,钴、镍、锰分别约90%、74%和50%。更为严重的是,预计未来20年内,该态势将持续加剧。
开发利用深海矿产资源,则是提高我国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的新途径。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来源主要是按照“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来布局。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日益加强,从国外进口资源将越来越受到制约。这种制约,来源于传统的陆地资源大国和西方国家强势的价格和规则。
而我国本土陆地资源的开发,同样困难重重——不仅受到储量的限制,而且也存在矿区开采条件和边远地区环境与民族问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深海采矿则可以比较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
“据初步测算,在一个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内,推测的结核资源量约为4亿吨,其中含铜约400万吨,钴约100万吨,镍约500万吨,锰约1亿吨,可支撑一个年产300万至500万吨、开采15年至20年的深海采矿项目。”金建才说。
但是,与巨大的开采需求极不匹配的,是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能力的严重不足。
据专家介绍,20多年来,我国尽管已经开展了深海采矿研究,但主要还是结合国际海域矿产资源勘探工作开展的,迄今尚未形成资源开发的技术能力。
其一,是尚未开展深海采矿规模化的技术能力验证。
金建才介绍,目前,我国虽已研制了部分试验设备,并于2001年进行了部分采矿系统湖上试验,但一直未能开展海上试验,与西方国家30年前便已成功完成 5000米级采矿海试相比,落后甚远,甚至已落后于印度与韩国(近年来分别进行了500米和200米的浅海试验)。由于没有系统地进行海上试验验证,系统设计无法确立,更谈不上自主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
其二,是远未形成深海采矿产业化的协同工程体系。仅从产业化所必备的工程化能力而言,深海采矿系统庞大,涉及矿业、冶金、重型装备制造、船舶、海洋工程及环境管理等多个行业与部门,需要多部门的协同推进。
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深海采矿能力可在数年内形成”的基本预判。专家们一致认为,根据这一预判,在商业性开采即将到来之际,如不迅速采取措施,我们将面临无力也无从应对的被动局面。
总之,我国深海采矿的能力建设严重滞后。
“与主要海洋强国相比,我们在组织机制上缺乏以企业为主体的运作方式,在能力支撑上缺乏以船舶平台为主的保障能力,在人才队伍上缺乏稳定的以深海采矿工程技术团队为主体的中坚力量。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在国家战略层面以深海采矿工程为核心的长期目标引领和重大任务支撑。”金建才对记者分析。
对策
尽早培育深海采矿产业
事实上,我国的深海采矿技术研究,既缺乏明确的国家重大专项支持,又没有获得相关企业的重视和投入,直接导致了我国深海采矿技术发展滞后,也影响了深海采矿工程技术研发人才队伍的形成和稳定。
对需求巨大但能力不相匹配的现状,专家建议,应尽早谋划和加快布局我国深海采矿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越性,谋取后发优势。
其一,启动深海采矿工程。搭建深海采矿技术能力发展和产业培育的平台,发挥中国大洋协会的协调组织作用,聚集全国优势力量,以完成6000米级深海采矿系统海上试验为总体目标。
“按照由浅入深、由近至远、分步实施的原则,争取在10年内,分1000米、3000米、6000米级三个阶段,实施我国的深海采矿工程,为在国际深海商业采矿时机到来时,形成我国深海采矿技术能力和培育深海采矿产业,奠定坚实基础。”金建才设想。
其二,建立以企业运作为主的新机制。确立企业是深海资源开发与深海技术装备创新的主体地位,通过政策支持和机制创新,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加大深海采矿产业培育力度,以推动“适时建立深海产业”的大洋战略目标尽早实施。
金建才认为,在建设海洋强国宏伟目标的指引下,应锁定深海目标来提高海洋资源的整体开发能力,“国家对深海采矿的投入规模首先取决于对深海作为发展空间、技术前沿和资源保障等战略地位的认知程度。”
另外,深海采矿对环境认知水平的同步发展也有很高要求。“我们应开展环境基线调查和环境影响评价。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深海采矿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一位专家说。
数说深海采矿
“近年来,我国大宗矿产大量依赖进口,重要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铜约70%,钴、镍、锰分别约为90%、74%和50%。”
“据初步测算,一个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推测的结核资源量约4亿吨,其中含铜约400万吨,钴约100万吨,镍约500万吨,锰约1亿吨,可支撑一个年产300万至500万吨、开采15年至20年的深海采矿项目。
“争取在10年内,分1000米、3000米、6000米级三个阶段,实施我国的深海采矿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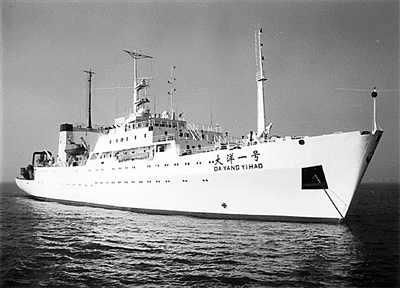

“蛟龙号”在中国大洋协会富钴结壳勘探矿区拍摄的不同生物种群。 (资料图片)
“蛟龙”探海,威风八面;同时拥有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这三种主要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专属勘探矿区,目前在国际深海采矿界还是唯一;深海勘查,持续见效,让国际同行为之赞叹……
几代海洋人对海洋强国梦的苦苦追索,让我国在深海资源勘探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是,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说,我们的脚步还是慢了一点。
9月16日,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尽管目前深海资源勘探活动仍十分活跃,但国际海底活动的重心已然向资源开采阶段过渡,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
“近年来,国际上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日趋活跃,并呈现出具有深远意义的新动向。一些跨国企业的深海采矿计划正在或已经付诸行动,深海采矿产业端倪显现,形势逼人。”在会议间隙,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金建才对记者说。
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在这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与海洋强国的差距十分明显。“如果在这一步落后,就会步步陷于被动。而要迎头赶上,须从现在开始努力,须臾不能松懈。”一位业内专家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表示。
国际
准备充分且行动加速
一个事实已经不容否认:当我们还在资源勘探领域埋头苦干的时候,一些国家和国际矿业企业,已经对深海矿产资源的开采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
这依靠两股力量的推动:一股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陆地上的资源供给已经越来越乏力;另一股力量,则是海洋技术不断发展,深海采矿的技术和理念获得新突破。对深海采矿来说,技术的羁绊,显然已经越来越弱。
公开的报道显示,自2012年10月以来,一些涉及深海采矿的国际会议相继在中国举办,包括国际深海采矿第四十一届年会、第三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与法律问题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八十二条执行问题国际研讨会。
“这些会议,以深海采矿为主题或重要议题。关于海洋采矿可能比陆地采矿更环保、社会与投资效益更高等一些新理念和观点,正逐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对发展深海采矿,国际上不仅有殷切的期望,而且无论从技术支撑还是商业盈利的角度考虑,信心都越来越足。”金建才说。
业内的一系列动作,也在不断增强这个信号。
实际上,在2012年国际海底管理局第十八届会议上,制定深海采矿规章已被作为优先事项列入2013年的工作计划中,并期望于2016年前制定 (多金属结核)开发监管规则。其中重要动因之一,是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一批7个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将于2016年到期。
而欧盟前不久制定的《蓝色增长:海洋可持续增长的机遇》报告也明确提出,目前欧洲应主要集中研发各种深海和海底特种船舶及采矿装置,为联合开采国际海底的矿产资源作好准备。
不难看出,国际社会正加快做好深海采矿产业发展的准备工作,无论是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战略部署上。“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国际矿业公司已行动起来,正积极推进深海采矿。”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
金建才告诉记者,在国际海底管理局成立并开始运作后的10余年内,只核准了8份矿区勘探申请。而从2011年至今,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有11份矿区勘探申请获得核准,另有4份矿区勘探申请待批,其中8份是西方矿业公司或其“借壳”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其商业目的十分明确。”
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和企业还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展了矿产资源勘探及开采准备工作。
记者了解到,2011年,加拿大鹦鹉螺矿业公司获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颁发的世界第一个深海多金属硫化物资源采矿租约,计划于2014年进行试开采。
2012年4月,该公司与我国铜陵有色集团签订海底矿石加工合作协议,每年向铜陵有色集团提供矿石110万吨,加工后的铜精矿全部销售给铜陵有色集团,合同期为3年,预计首次矿石交付时间在2014年。
此外,公开的资料显示,韩国的深海采矿财团也在汤加和斐济专属经济区内申请了矿区并进行资源勘探,计划于2015年进行一个年产30万吨规模的采矿海试。
“国际社会发展深海采矿产业,要具备两大要素——技术和市场。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两大要素已基本具备,而且推进形成这一新兴产业的行动在加速。特别是一些西方国际矿业公司,他们把中国作为未来深海采矿产品的首选市场,尤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金建才对记者说。
国内
需求巨大但能力不足
实际上,我国对深海矿产资源开发的需求同样巨大。
一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大宗矿产大量依赖进口,重要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铜约70%,钴、镍、锰分别约90%、74%和50%。更为严重的是,预计未来20年内,该态势将持续加剧。
开发利用深海矿产资源,则是提高我国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的新途径。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来源主要是按照“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来布局。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日益加强,从国外进口资源将越来越受到制约。这种制约,来源于传统的陆地资源大国和西方国家强势的价格和规则。
而我国本土陆地资源的开发,同样困难重重——不仅受到储量的限制,而且也存在矿区开采条件和边远地区环境与民族问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深海采矿则可以比较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
“据初步测算,在一个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内,推测的结核资源量约为4亿吨,其中含铜约400万吨,钴约100万吨,镍约500万吨,锰约1亿吨,可支撑一个年产300万至500万吨、开采15年至20年的深海采矿项目。”金建才说。
但是,与巨大的开采需求极不匹配的,是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能力的严重不足。
据专家介绍,20多年来,我国尽管已经开展了深海采矿研究,但主要还是结合国际海域矿产资源勘探工作开展的,迄今尚未形成资源开发的技术能力。
其一,是尚未开展深海采矿规模化的技术能力验证。
金建才介绍,目前,我国虽已研制了部分试验设备,并于2001年进行了部分采矿系统湖上试验,但一直未能开展海上试验,与西方国家30年前便已成功完成 5000米级采矿海试相比,落后甚远,甚至已落后于印度与韩国(近年来分别进行了500米和200米的浅海试验)。由于没有系统地进行海上试验验证,系统设计无法确立,更谈不上自主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
其二,是远未形成深海采矿产业化的协同工程体系。仅从产业化所必备的工程化能力而言,深海采矿系统庞大,涉及矿业、冶金、重型装备制造、船舶、海洋工程及环境管理等多个行业与部门,需要多部门的协同推进。
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深海采矿能力可在数年内形成”的基本预判。专家们一致认为,根据这一预判,在商业性开采即将到来之际,如不迅速采取措施,我们将面临无力也无从应对的被动局面。
总之,我国深海采矿的能力建设严重滞后。
“与主要海洋强国相比,我们在组织机制上缺乏以企业为主体的运作方式,在能力支撑上缺乏以船舶平台为主的保障能力,在人才队伍上缺乏稳定的以深海采矿工程技术团队为主体的中坚力量。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在国家战略层面以深海采矿工程为核心的长期目标引领和重大任务支撑。”金建才对记者分析。
对策
尽早培育深海采矿产业
事实上,我国的深海采矿技术研究,既缺乏明确的国家重大专项支持,又没有获得相关企业的重视和投入,直接导致了我国深海采矿技术发展滞后,也影响了深海采矿工程技术研发人才队伍的形成和稳定。
对需求巨大但能力不相匹配的现状,专家建议,应尽早谋划和加快布局我国深海采矿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越性,谋取后发优势。
其一,启动深海采矿工程。搭建深海采矿技术能力发展和产业培育的平台,发挥中国大洋协会的协调组织作用,聚集全国优势力量,以完成6000米级深海采矿系统海上试验为总体目标。
“按照由浅入深、由近至远、分步实施的原则,争取在10年内,分1000米、3000米、6000米级三个阶段,实施我国的深海采矿工程,为在国际深海商业采矿时机到来时,形成我国深海采矿技术能力和培育深海采矿产业,奠定坚实基础。”金建才设想。
其二,建立以企业运作为主的新机制。确立企业是深海资源开发与深海技术装备创新的主体地位,通过政策支持和机制创新,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加大深海采矿产业培育力度,以推动“适时建立深海产业”的大洋战略目标尽早实施。
金建才认为,在建设海洋强国宏伟目标的指引下,应锁定深海目标来提高海洋资源的整体开发能力,“国家对深海采矿的投入规模首先取决于对深海作为发展空间、技术前沿和资源保障等战略地位的认知程度。”
另外,深海采矿对环境认知水平的同步发展也有很高要求。“我们应开展环境基线调查和环境影响评价。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深海采矿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一位专家说。
数说深海采矿
“近年来,我国大宗矿产大量依赖进口,重要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铜约70%,钴、镍、锰分别约为90%、74%和50%。”
“据初步测算,一个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推测的结核资源量约4亿吨,其中含铜约400万吨,钴约100万吨,镍约500万吨,锰约1亿吨,可支撑一个年产300万至500万吨、开采15年至20年的深海采矿项目。
“争取在10年内,分1000米、3000米、6000米级三个阶段,实施我国的深海采矿工程。”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43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433号